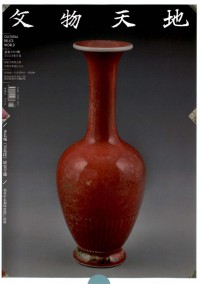考古學研究匯總十篇
時間:2023-12-24 16:28:12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考古學研究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別介紹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大型動物和小型動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綱、鳥綱、爬行綱、兩棲綱、軟骨魚綱和硬骨魚綱等脊椎動物以及軟體動物和甲殼綱等無脊椎動物。微型動物是指以上各類動物中個體較小的種類,如蝸牛、昆蟲等。動物考古學的研究目標是探討人與環境,特別是人與動物的關系。在人與動物的關系中,人類利用動物是主要內容,如以動物為食;用動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體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進行勞作和運輸,用狗協助打獵、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動物融入人類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圖騰等觀念。動物考古學的特點是多學科的交叉性,在研究過程中需要運用生物學、生態學等自然科學和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等社會科學的知識。
二、 動物考古學的歷史和理論
作者在第二章簡略回顧動物考古學的發展歷史。19世紀,美國考古學者注重對器物分類和描述,動物遺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對生物學感興趣的學者完成;之后,研究環境的生物學家開始注意動物遺存,他們研究動物的分布、滅絕的種類、骨骼形態特征和病理學,也有學者推測人類行為并收集、鑒定并測量骨骼。20世紀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學家的重視,被加工的骨器終于進入他們的視野。但是,沒有人工痕跡的骨骼仍然沒有得到重視。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與環境的關系的觀點,動物考古學才有了實質性的發展。隨后,最小個體數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動物考古學成為一門可認知的學科,在考古學研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在發展過程中,動物考古學不斷從生物學、人類學以及考古學中借鑒理論和方法。目前,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內容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如怎樣獲得準確的數據?二是人類學方面的研究,如人類的營養需求、生存策略、社會關系和家畜起源等問題;三是生物學和生態環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動物的生長、自然環境的面貌等。
三、 動物考古學的背景知識
動物考古學研究首先應具備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作者在第三章對生物學知識進行介紹。在分類學方面,動物考古學借用生物學中的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法,力圖將出土骨骼鑒定到種或屬。在解剖學方面,提到動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為攝食、運動和保護三種,功能的不同導致骨骼形態的不同。分布地域、季節和人類行為等外因和個體發育、年齡和性別等內因導致個體在骨骼上的差異,動物考古學家利用這些差異區別不同種屬和年齡階段的動物。生物不斷與外界物質發生交換,體內碳、氮等穩定同位素含量有變化,生物自身蘊含遺傳信息,因而碳氮穩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這類科技方法也被應用于動物考古學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紹了與動物考古學相關的生態學知識。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每種動物都有特定的生態位和生活史對策。生態位是指生物與其所在的環境發生的所有關系;生活史對策在不同的環境中會有變化,它包括動物的繁殖、生長和發育、性成熟、照顧幼崽和衰老等方面。這對古代人類的狩獵活動很有幫助,可以被動物考古學家用來推測人類當時的行為。在有機物質和無機物質相聯系的生態系統中,生物因素、食物網、生產率、豐度、多樣性和均勻度是群落生態學要研究的問題。關于均勻度,我國有學者對其在動物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有過介紹(1),還有學者用分異度和均衡度分析遺址周圍的野生動物資源,進而探討人類的生業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講述動物骨骼在人類使用遺址時、遺址被廢棄后、考古學家發掘及整理時發生的埋藏學變化。骨骼發生的埋藏學改變分為初期變化和后續變化兩種。初期變化發生于動物被捕獲、人類利用動物、骨骼被掩埋的過程中;后續變化是發掘和整理資料時造成的變化。古代人類的某些行為是一級改變的原因,如捕捉動物、宰殺動物、剝皮、肢解、烹飪、燒烤、制作工具等。我國學者曾通過實驗觀察人類吸髓與動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動物的一些行為,如食肉動物和嚙齒類動物啃咬、大中型動物踩踏等,以及氣候、溫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誘因。除需要注意初期變化,后續變化對動物考古學家進行解釋也有影響。以發掘方法為例,是否采用篩選法或浮選法,對發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響,進而影響鑒定結果和結論。
四、 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談到怎樣從眾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價值的信息、應該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將這些信息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鑒定骨骼直接獲得的信息,稱為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可以被后來的研究者重復觀察;另一種是衍生資料需要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通過分析和計算得到。原始資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種屬、數量、表面痕跡、病理現象、年齡和性別的解剖學特征、測量數據和重量等。這些內容最后都要輸入電腦,以便進行各種計算。在鑒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資料,準備當地的動物標本。鑒定過程中要持謹慎的態度,使用解剖學語言描述骨骼的具體部位、特征和保存狀況。反映年齡的特征主要有頭骨縫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齒萌出和磨損的程度,反映性別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態。可鑒定到種屬的骨骼數量和不可鑒定的骨骼數量都要統計。觀察骨骼表面痕跡要記錄骨骼斷裂的位置、斷裂面方向、斷裂口的形狀。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態不正常的牙齒或骨骼以及牙齒是否發生釉質發育不全的現象。比較完整的骨骼需要測量。由于原始資料是衍生資料的基礎,所以需要熟練的人員從事鑒定的工作。
如何獲取衍生資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內容,包括估算個體大小、建立年齡結構和性別比例、計算各種動物的相對比例和骨骼的出現頻率、估算古代人類的食物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跡和病理現象等。
了解動物的個體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類喜歡捕獵哪種體型的動物、被捕捉的動物群是否存在狩獵壓,也可以評估肉類在食物中的比重。復原個體大小最簡單的方法是將骨骼與實驗室的現生骨骼標本比較,大小基本一樣的標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動物大小。測量值也可為區分動物個體大小提供標尺,還可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
在原始資料中記錄的年齡特征可以反映個體大概的死亡年齡,多個個體的死亡年齡可以建立這一種動物的年齡結構曲線。生存曲線可以解釋人類的某些行為:死亡年齡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線提示人類飼養它們的目的是為了吃肉。骨骼形態特征和測量數據可以反映動物的性別,成年的雄性個體往往大于雌性個體。同年齡結構一樣,性別比例也提示人類行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選擇的一種結果。
通過最小個體數和可鑒定標本數能夠計算遺址內一種動物占所有動物的數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類經常利用哪些動物。如果某種動物占的比例極大,那么這種動物就很有可能是家養動物。計算最小個體數的方法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變化,懷特(White)認為可以利用左右兩邊對稱的骨骼來估算最小個體數,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邊的數量多,其值就是最小個體數。隨后有學者將年齡、性別、骨骼大小這些因素補充到計算最小個體數的考慮要素中。例如,發現2塊豬左側的下頜(1塊1歲,1塊2歲),1塊右側的下頜(3歲),可見右側的那塊下頜與左側的2塊都非一個個體,因此最小個體數應該是3。此外,可鑒定標本數也是統計數量的方法,它是由計算分別屬于各個種屬的全部動物骨骼數量得來的。與最小個體數不同,可鑒定標本數有時容易受到一塊完整骨骼破碎成多個碎塊的影響,應而在研究遺址出土的各個種屬的動物數量時,應綜合兩者進行分析。
計算骨骼的出現頻率要先將骨骼歸納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鎖骨;也包括多塊骨骼連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學部位,如前肢、腳;還包括人類屠宰動物經常肢解的單元。最小個體數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數量,最大值就是這個遺址預期收集到的值,每個部位發現的數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發現值與預期值的比例。我國已有學者對遺址內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現的頻率做過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數也是研究骨骼出現頻率的一種方法。
有兩類方法從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類的食物組成。第一類方法是估算一個完整個體的肉量。懷特(White)通過文獻并結合具體實例考證鳥類身上的肉量占總重量的70%,哺乳動物的占50%。用每種動物的體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這種動物的肉量。一個個體的肉量乘以最小個體數,可以求得這種動物對古代人類肉食貢獻的總量。第二類方法由里德(Reed)發明,根據出土骨骼的重量復原肉量。我國有學者針對這兩種計算方法做過比較研究,認為它們具有不同的適用范圍⑤。
骨骼表面痕跡的位置和類型以及病理現象可以提供人類行為的信息。出現在關節連接處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動物時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現象可能是勞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風化程度可以為埋藏學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動物考古學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難看出每種方法可以解決相對應的研究問題,因此研究方法應與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過程中還要充分考慮到每種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謹慎的、客觀的推斷。
五、 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別談了動物考古學中比較重要的三個研究問題,第八章探討如何解釋古代人類狩獵形成的動物遺骸和人類的生存策略。人類在捕獵時需要考慮哪些因素?約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們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種動物資源、用多少、什么時候找、到哪找、由誰找等問題。這一模型的本質是古代人類在獲取動物資源時花費的支出和最終的收益之間尋找平衡。古代人類選擇居住點、進行捕獵等生存活動需要考慮是否受限于時間、空間等環境條件。我國膠東半島貝丘遺址的動物考古學研究顯示,由于人類活動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圍內持續捕撈對貝類的生長造成捕撈壓⑥。當人類狩獵成功后,他們選擇價值高的部分帶回居住區,開始制作食物。這個過程會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跡,也會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質等微小物質。人類還會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裝飾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隱藏在可以觀察到的動物遺存的背后,還有當時與人類狩獵活動有關或是因狩獵活動形成的交換系統和社會地位、社會組織、等各種社會關系,動物考古學家試圖用物質遺存來探尋這些背后的聯系。
古代人類馴養家畜的活動也是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問題。第九章主要講人類馴養家畜、利用家畜的行為以及怎樣初步鑒定家養動物。狗是一種獨特的家養動物,它被馴化的時間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態可以與野生祖先相區別,而DNA研究顯示家狗起源的時間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衛居住地、幫助狩獵、陪伴人類,還能幫助人類看守家畜。其它的家養動物可以為人類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動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裝飾品的原料,動物的糞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還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動物犧牲等。多數家養動物的體型逐漸變小;身體各部分的比例也發生變化,如豬的鼻子變小。骨骼測量是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一種方法。另外,還可以在測量的基礎上計算骨骼的長寬之比。數量比例、年齡結構、性別比例和病理現象也能夠提供人類馴化的信息。羊毛紡織品、家畜和柵欄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類成功馴化并利用家養動物的佐證。我國學者依據中國動物考古學的實踐,提出了考古遺址出土家養動物的系列鑒定標準⑦。
用動物遺存重建古代環境是動物考古學中研究歷史相對較長的一個問題,早在動物考古學發展之初,古環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開展了這方面研究。用動物遺存復原環境的理論基礎是均變論,即“將今論古”。在了解現代動物的生活習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礎上,推知古代的動物也具有這樣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遺址出土的物種復原當地的自然環境和氣候。例如,竹鼠現在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和長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竹鼠的骨骼,這說明當時的氣候比現在溫暖濕潤⑧。這一過程要區分遺址當地的物種和外來的物種,復原遺址周邊環境時應排除外來物種。小型動物對環境變化敏感,提供的生態學信息較多。寄生蟲還可以提供人類生活條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種種群內部若干個體的體形大小和年齡可以判斷當時的環境是否有利于動物生長。古代人類不斷向自然環境索取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環境,最顯著的行為就是動植物的馴化影響到原來生態系統的平衡,這也是復原環境的一項研究內容。
六、 結 論
第十一章是全書的結論,作者列出埋藏學、營養和飲食、動物資源的利用、技術、交換系統、社會等級、馴化和古環境八項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資料、衍生資料和與之相聯系的理論、觀點,簡明地表示了從骨骼獲取信息與進行考古學解釋之間的關系。作者強調研究者應持謹慎的態度和方法,使用與研究目標匹配的研究方法,通過觀察、實驗和重復的方法,將多學科的研究綜合起來。作者指出,目前動物考古學研究在研究方法、人類對環境的適應和影響、動物的用途和社會含義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學的應用將在動物考古學研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整合這些研究才能從更廣泛的角度研究人類的歷史。
這本教材從動物考古學研究需要具備的相關知識入手,分別講述了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研究內容,幫助讀者對動物考古學有一個初步了解。然而,《動物考古學(第二版)》以美國及其附近地區的研究為主,沒有收錄我國動物考古研究的資料,不利于初學者掌握我國的研究歷史和現狀。動物祭祀和隨葬是我國動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如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使用豬進行隨葬和祭祀的現象⑨,漢水中游地區史前墓葬隨葬豬骨的現象可能與社會分化有關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規格遺址祭祀用牲的種類是不同的(11),該書對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為一本入門指導的教科書,《動物考古學(第二版)》值得初學者精細地研讀,從而掌握這一分支學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為做好我國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奠定基礎。
我在學習動物考古博士課程的第一年,導師袁靖先生要求我閱讀英文版的《動物考古學(第二版)》,還要求每讀完一段話,要用中文記錄下這段話的大意。經過一個學期,我終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閱讀和記錄的過程中,我對動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認識,在隨后的鑒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這些認識又得到進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謝袁靖先生帶我走進了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謝《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著者編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遲遲沒有發表,現在正好趕上《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中譯本即將出版,我相信會有更多的人從閱讀《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譯本的過程中受益!
注釋:
① 胡松梅:《分異度、均衡度在動物考古中的應用》,《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黃蘊平:《動物骨骼數量分析和家畜馴化發展初探》,《動物考古(第1輯)》,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呂遵諤、黃蘊平:《大型肉食哺乳動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馬蕭林:《靈寶西坡遺址的肉食消費模式――骨骼部位發現率、表面痕跡及破碎度》,《華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楊杰:《古代居民肉食結構的復原》,《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錕宇、蔣成、陳劍:《淺論動物考古學中兩種肉量估算方法――以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為例》,《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5期。c.羅運兵:《中國古代豬類馴化、飼養與儀式性使用》,第50頁,科學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膠東半島貝丘遺址環境考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國古代家養動物的動物考古學研究》,《第四紀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韓德芬:《陜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之獸類骨骼》,《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59年第4期。
篇(2)
自近代考古學的方法和技術傳入之后,中國錢幣學界不再滿足于“忽略制作,偏重文字,斤斤于色澤肉好,戚于珍常多寡,范圍狹隘”的簡單的經驗型研究。1936年,由葉恭綽、吳稚暉、丁福保等組織成立中國古泉學會,其創辦的會刊《古泉學》第一期中提到了其宗旨,“以闡明古泉學識,研究古泉制作,鑒定真贗,辨別年代,啟人好善之心為宗旨”,這反映了當時古泉學研究的對象有所擴展,已經開始注意錢幣的制作了。1940年,丁福保組織成立中國泉幣學社,提出研究錢幣須“按諸貨幣原理,以究其制作沿革,變遷源流,利病得失之所在,治亂興替之所系”。(張N伯《本刊發刊詞》,見《泉幣》第一期)盡管民國以來考古學已經傳入,對古錢幣的研究的認識有所突破,但是古錢幣研究仍然比較沉寂,此時期出版的書籍,如《古錢大辭典》、《歷代古錢圖說》等,仍然具有圖譜的性質。直到1954年彭信威先生的《中國貨幣史》問世和1989年后中國錢幣學理論體系的提出,對古錢幣的研究才更加科學,中國錢幣學逐漸成熟、繁榮。
從1954年至1989年之間,有一本著作不僅在考古界影響重大,被譽為有“中原漢墓編年可資借鑒的標尺”,同時在錢幣學界的影響也非常重大,是考古學與古錢學結合起來的經典,那就是由蔣若是先生主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科學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洛陽燒溝漢墓》。
在《洛陽燒溝漢墓》一書,以科學的考古學方法,解開了號稱歷史貨幣研究的“謎團”――五銖錢分期斷代,此后的半個世紀以來,對五銖錢的斷代基本都沿襲此書的方法,并且被多次證明結論的正確。那么《洛陽燒溝漢墓》何以能夠解決這一個千百年來的謎團呢?這就需要仔細閱讀一下此書了。
《洛陽燒溝漢墓》一書是1953年洛陽燒溝區發掘的255座漢墓的報告,報告分為序言、第壹編、第貳編、第叁編、第肆編、結論和編后記,著重研究了漢代墓葬的墓室結構和陶器、銅器、鐵器、鉛器、玉石器等等器物類型的發展演變及分期依據,建立起中原地區漢代墓葬的年代標型序列,給漢代物質文化史研究也提供了寶貴資料,其中就包括對255座漢墓出土的11267枚錢幣的分析、研究。
《洛陽燒溝漢墓》在第叁編第十章專門對出土的錢幣進行了研究,從錢幣的形制、年代、與墓型的關系三個方面展開。在這些錢幣當中,從時代上看有秦、西漢、新莽及東漢的錢幣,種類有半兩、五銖、新莽錢及雜錢,除了一枚鐵質、一枚鉛質外,其余都為銅質。
書中對半兩的分型比較簡略,分為三型(圖1),根據墓葬年代、文獻記載及大小輕重關系,認為第一型為秦半兩,第二型為呂后半兩,第三型為文帝半兩,但是在第四、五型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半兩第三型出土,即是說第三型半兩是東漢晚期的。但是在書中227頁的表五五中,沒有分型說半兩的年代,而且表中表示的半兩流行時代只有武帝、昭帝、宣帝及桓帝、靈帝時期,在武帝、昭帝、宣帝時期是非正式通行期,在昭帝、宣帝時期雖非正式通行期但是流通仍很多。這樣的結論是客觀的,只是沒有對半兩的類型與時代對應起來有一點遺憾。
但是對于五銖的分型分期卻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洛陽燒溝漢墓出土的五銖錢,最早的起武帝中、晚期,下限到東漢末,數量眾多、差別微小的錢幣,非下一番苦功夫不能夠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書中以墓葬及遺存的年代(包括墓葬結構、共存遺物及出土情況)為主要的判斷依據,結合文獻、類型學、圖像學方法進行分析(包括對錢幣的文字、形制及錢范的考證),綜合考察并確定隨葬五銖錢的歷史年代。先對五銖錢類型的相對年代考察,再分別對五型的絕對年代進行判定,客觀嚴謹。
將五銖分為五型(圖2):第一型為武帝到昭帝時期,“五”字中間相交兩筆為直筆的是武帝時期的,昭帝時期的稍彎曲,“銖”字“金”頭為鏃形,多不清晰,“朱”字頭方折;第二型為宣帝至西漢末,“五”字兩筆彎曲(越晚的越彎曲),“銖”字同前無大的變化,但字劃清晰;第三型為東漢前期,字體較寬大,金字頭較前為大,如三角形,“朱”字頭圓折;第四型屬于東漢中晚期(桓帝及以后),各種特點基本同于東漢前期的三型,只是較薄,文字輪郭更淺平,并帶有陰文或陽文符號;第五型為靈帝時期,背有四道內外郭相連的四出文是其主要特征。
“前人定五銖錢年代,說多無據,惟“四出”為有據,有由據者推之,知無據者盡臆說矣。”清代戴熙若是看到蔣若是先生提出的五銖分期斷代,定不再有此感嘆。此外還有一些地域或時代特征的五銖錢幣。(圖3-1、2)
這一成果概括了各個時期五銖錢的基本特征,讓行用時間長達700多年的五銖錢分期斷代有了科學可靠的根據,歷經半個世紀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所以說,這是一本將考古學方法應用于研究古錢幣、將古錢幣研究納入考古學范疇的重要著作,在古錢學和考古學中都意義重大。
當然在五銖錢的分期斷代研究上,《洛陽燒溝漢墓》也有不足。但是這是由于非錢幣學專著,沒有深入探討,由于燒溝漢墓墓葬時代等客觀條件的限制,《洛陽燒溝漢墓》提出的分期標準不能面面俱到,它對早期五銖錢的類型認定有些不足,例如郡國五銖、赤仄五銖、上林三官五銖。
篇(3)
考古遺址中的一些遺跡現象可能與人類利用昆蟲有很大的聯系。民族學資料顯示,人類捕殺昆蟲時會在地上挖條淺溝,把大批昆蟲吸引過來,然后放火燒烤。Weaver和Basgall在加利福尼亞的一處遺址發現一條寬約53厘米的淺溝,他們認為這與捕獲毛蟲有關(6)。此外,古代人類還利用一些石質工具制作昆蟲食物。Flood用紫外線照射石器發現上面的蛋白質是制作毛蟲留下的。使用氣相或液相色譜分析能夠發現殘留在容器內壁的與昆蟲相關的遺物,如蜂蜜和蠟(7)。Meighan C.W. 在加利福尼亞中部的一處遺址里發現了一條鏈子,是用甲蟲腿做成的一百多顆小珠子穿成的,這可能是一種與宗教有關的裝飾物(8)。
如同遺址出土的那些用來推測自然環境的動物骨骼一樣,昆蟲也可以為自然環境的變化提供證據。有些昆蟲體型很小,對環境很敏感,是重建自然環境的重要材料。特別是甲蟲,當環境發生變化時,它傾向于尋找新環境而不是適應舊環境;它分布廣泛,相對容易保存,是學者常研究的昆蟲。Osborne根據英國南部威爾特郡Wilsford青銅時期豎井出土昆蟲的種類,復原了當時的氣侯和生態環境(9)。從昆蟲的種類來看,Osborne認為英國南部當時的氣候和現在的氣候基本一樣,或是稍偏暖一些;出土的甲蟲數量很多,這暗示當地存在大量食草動物,應該有遼闊的草地;一些昆蟲喜光,所以當地的陽光充足,樹木不多,草地相對干燥。
Osborne還對豎井出土的昆蟲遺存做出考古方面的解釋。甲蟲的數量很多,在發現的昆蟲中占的比例很大,表明有很多食草動物被限制在或因其它原因出現在豎井周圍。較為干燥的草地也許暗示存在綿羊,但是如果這個豎井是取水用的,那么也可能存在牛。考慮到出土的昆蟲較為集中,而且數量很多,這里養牛的可能性更大。庭院葉麗(Phyllopertha horticola) 是外來的物種,這類昆蟲生活在長莖的草地中,可能是人類收割長莖的草作飼料時將它們帶入到豎井的周圍。家具竊蠹(Anobium punctatum)寄生在死樹上,所以豎井周圍還存在木頭。Osborne通過研究昆蟲推測了當時的情形:豎井上有木質水槽或是其它結構用來打水,周圍有柵欄圈住家畜。
Eva Panagiotakopulu在利物浦博物館收藏的古代埃及人的食物和樹膠上發現了昆蟲,有鞘翅目的谷蠹、藥材甲、錐胸豆象和一種屬于雙翅目的蛹殼。研究者對這些昆蟲進行分析,探討它們的地理分布、危害哪些農作物。這些昆蟲的出現說明古代遺物遭到了害蟲的感染。而且,博物館收藏的其它埃及和近東地區的食物標本里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害蟲感染的現象。研究者認為這些昆蟲的出現為生物地理學和古代人類儲藏的產品遭受害蟲感染的歷史提供信息,同時還呼吁更多的考古學家關注這一問題(10)。
昆蟲遺存可以提示遺跡現象的時間信息,Gilbert和Bass根據墓葬人骨上附著的蒼蠅蛹推測這些尸體被埋葬的時間(11)。在距今100多年的美國阿里卡拉人墓葬中,發掘者在死者身上發現很多蒼蠅蛹,多在頭部和腹部出現。動物死亡不久蒼蠅就會在尸體上產卵。當地在每年3月到10月中旬有蒼蠅,Gilbert和Bass由此推斷這些附著蒼蠅蛹的尸體是在這幾個月內下葬的。
一些昆蟲,例如虱子,棲息在人的生活環境里危害人類的健康,因此昆蟲遺存還可以反映古代人類的衛生條件。人虱(pediculus humanus)寄生在人體頭上和身體上,可以在梳子和衣物上大量存留,而陰虱(Pthirus pubis L.)不如人虱容易保存下來。Kenward對中世紀英國一處遺址發現的陰虱做了研究(12)。以往研究者猜測英國的虱子是從英國以東的地區傳入的,但是在英格蘭坎布里亞郡Carlisle遺址發現虱子顯示它們在中世紀時期已經在英國開始了寄生的生活。
Sutton在《Archaeological Aspects of Insects Use》中還提到昆蟲對遺址形成過程的影響,引用幾個埋藏學研究的案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綜上所述,研究考古遺址出土的昆蟲可以復原氣候和生態環境,為遺跡形成的時間或季節、古代人類的健康水平、古代生物的地理分布和分析遺址的埋藏過程提供信息,還可以為家畜的存在提供佐證。
以上研究離不開田野發掘過程中收集昆蟲樣本的重要環節。國外學者通常采取田野采集土樣、在室內提取的方法收集昆蟲遺存。發掘中提取每層剛剛暴露的土壤,放入塑封袋中,寫好出土單位。帶回實驗室后,根據不同的研究目的采用不同的方法提取昆蟲遺骸。最常用的方法是篩選,但是這里用到的網篩要比以往篩選動物骨骼的網篩小得多。Buckland和Coope認為篩孔為0.3毫米的網篩可以收集到大部分昆蟲,一些特別細小的部位需要使用篩孔為0.1毫米的網篩(13)。篩選后的土壤要經過水洗或是化學物質的溶解,看是否還能發現昆蟲遺骸。下面是一個因為采用不同大小篩孔的篩選網而改變研究者結論的事例:Madsen和Kirkman發掘Lakeside洞穴遺址時,使用篩孔為1/4英寸(1英寸=25.4毫米)的網篩篩選后得到很少的蝗蟲個體,他們認為當地古代人類沒有利用昆蟲。回到實驗室后,他們把取樣的土壤用篩孔為1/4英寸的網篩選,得到28只蝗蟲個體;經過篩孔為1/8英寸的網篩選,得到1750只蝗蟲;當他們選擇用篩孔為1/16英寸的網篩選,得到8772只蝗蟲。這一發現使他們改變了原有看法,從而認為蝗蟲是古代人類的食物的一部分(14)。
整理昆蟲遺骸的方法和整理動物骨骼的方法基本一致。首先要把后期侵入的昆蟲排除在外。其次,昆蟲遺骸一般放在顯微鏡下觀察,鑒定出種屬、年齡,有可能的話性別也要鑒定。鑒定時要比對圖譜和昆蟲標本。較為常見的是昆蟲的頭部(head)、前背板(pronotum)和翅鞘(elytra),有時也會碰到腿、腹部和生殖器(15)。然后統計最小個體數和可鑒定標本數,估算這些個體可以提供的食物總量。最后,在解釋昆蟲遺存時,要把它們放入考古背景中去分析。
目前,我國的考古發掘工作很少收集昆蟲遺骸,原因之一是昆蟲個體往往很小,混在土里肉眼很難發現。提取植物遺存的浮選法也許可以用來提取昆蟲遺骸。青海大通長寧遺址采集的土樣經過浮選后,研究者發現了炭化的昆蟲(圖一)。
除了采集方法,動物考古中的昆蟲研究還需要與植物考古學中的某些研究聯系起來。例如,在Eva Panagiotakopulu的研究中,人類儲藏的農作物會出現被昆蟲感染的現象;在Osborne研究豎井的案例中,昆蟲提示人類使用草料喂養牲畜;專門生活在一些蔬菜、樹木上的昆蟲可以反映植物的種類。所以,這項研究需要結合植物考古學的方法和知識,采用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思路來復原人類的歷史。
雖然我們目前掌握的人類利用昆蟲的資料都來自于歐美地區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的研究,在中國還沒有展開針對昆蟲的動物考古學研究,但是只要我們有意識地去推動這方面的工作,相信昆蟲作為動物考古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后也能夠逐步發展起來。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員和李志鵬博士為本文提出寶貴意見!
注釋:
(1) Josephine Flood. (1980). The moth hunters: Aboriginal Pre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Alp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 New Series No.14, Canberra.
(2) Mark Q. Sutton. (1995). Archaeological Aspects of Insect Us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2, No.3, pp. 253~298.
(3) 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譯:《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文物出版社,2004年。
(4) Darna L. Dufour. (1987). Insects as food: A case study from the Northwest Amaz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89, No.2, pp.383~397.
(5) Frison C. George, Marion Huseas. (1968). Leigh Cave, Wyoming, Site 48WA304. Wyoming Archaeologist 11, pp.20~33.
(6) Richard A. Weaver, A., Mark E. Basgall. (1986). Aboriginal exploitation of pandora moth larvae in east-central California, Journal of California and Great Basin Anthropology, 8, pp.161~179.
(7) S. Needham, J. Evans. (1987). Honey and dripping: Neolithic food residues from Runnymede Bridge. Oxford Journal of Archeaology 6, pp.21~28. van Balgooy, Josephus N. A. (1983). Chemical analysis of residue from a stone bowl. In Rector, C. H., Swenson, J. D., and Wilke, P. J. (ed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at Oro Grande, Mojave Desert, California, San Bernardino County Museum Association, Redlands, pp.178.
(8) Meighan, C. W. (1955). Excavation of Isabella Meadows Cave, Monterey Coun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Reports 29, pp.1~30.
(9) P.J.Osborne. (1969). An Insect Fauna of Late Bronze Age Data from Wilsford, Wiltshire.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Vol. 38, pp. 555~566.
(10) Eva Panagiotakopulu.(1998). An Insect Study from Egyptian Stored Products in the Liverpool Museum.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84, pp.231~234.
(11) B. Miles Gilbert, William M. Bass. (1967). Seasonal dating of burials from the presence of fly pupae. American Antiquity, Vol.32, No.4, pp.534~535.
(12) Harry Kenward. (1999). Pulic lice (Pthirus pubis L.) were present in Roman and Medieval Britain. Antiquity 73, pp.911~915.
篇(4)
小珠山一期和二期單一的器類和簡單的區別,似乎說明了小珠山文化類型早期文化因素的單薄與脆弱,其實不然。這種具有特質的“土著”筒形罐從發軔至發展,貫穿三代至戰國早期⑤。而壓印“之”字紋嬗變為列點式乃至幾何式的刻劃紋,始終維系其中,因為它是幾千年傳統文化思維的物化,因而成為難以替代的主要文化因素之一。這又充分說明了這種文化因素的發展與強大。至小珠山三期這種主流文化元素依然強盛的同時,卻發生了來自渤海南部山東半島大汶口文化強大的北上文化沖擊。
這種文化沖擊直接導致遼東半島地區南北強強文化的“融合”,致使其社會文化諸多層面發生了質的飛躍。首先表現在生活方面。大汶口文化北上與當地原住居民接觸雜居導致文化上的融合,形成了多樣的生活模式。生活用具的器類一改以往單一的以筒形罐為主,出現了多種器類。以郭家村遺址③④⑤層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器類為例⑥。ⅡT1H8:19鬶,深腹罐形,寬帶鋬,斜平流,錐狀足。ⅠT9③:22觚,僅存底部,平底。ⅠT6③:11豆,擴盤,粗柄,圈足。ⅠT6④:10盂,卷沿,腹頸偏下,平底,紅地紅彩,飾直線和斜線組成的網格紋。ⅡT5⑤:23盆形鼎,盆形,錐形足,小平折沿。除此之外,還有壺、碗、缽、杯、器蓋等。紋飾上出現了彩陶,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紅地黑彩,多數為斜線三角紋(ⅡT1③:25、73T2③:10)和雙勾渦紋(ⅡT8⑤:38),有的黑彩與刻劃紋組合成復合紋飾(ⅡT7③:25)。另一種是紅地紅彩,多為直線、斜線和三角紋(ⅠT4④:20、ⅠT3③:29、ⅡT7③:25、73T2③:19)。在所出土的各種器類的統計中,罐類36件,其中傳統的筒形罐就占有29件,可見在強大外來文化沖擊下,具有土著因素的傳統文化并未退出先主的地位。但多種類型及多種色彩紋飾的涌進,所表現的進步的或先進的諸多文化因素,預示著本土傳統文化存在的危機。生產方面出現了多重并進的發展態勢。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領先于周邊地區,而它的到來同樣帶來了包括農業生產在內的各領域的先進技術。除斧、雙孔刀(ⅡT6⑤:12)增多外,還出現了鐮(ⅡT2④:3)等一系列農業生產工具,磨盤、磨棒出土居多,分別為15件和23件,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時的農業生產規模,使本來薄弱的農業生產,發展成為占主要經濟地位的社會經濟形態。
農業生產的發展直接導致居住人口的增多,豐衣足食成為保障社會發展的第一要素。大量的紡織縫紉工具成系列的出現是此時文化發展的又一標識。有陶紡輪、骨錐、骨針、骨梭和角錐等,其中陶紡輪和骨針最多也頗具特色。陶紡輪出土142件,多是專門制作而成,少見陶片制成。陶紡輪的輪面多飾各種刻劃紋,有人字紋、花瓣紋、葉脈紋、列點斜線紋等,基本與陶器上的紋飾相一致(ⅡT6④:17、ⅡT5⑤:13、ⅡT8⑤:19)。點與線的組合在紡輪旋轉的律動中,給人以放射性的美妙的視覺感受,易于增強人們對“實”與“空”的靈動想象力和創造力。骨針出土129件,有圓錐形,尾扁平,對鉆孔(ⅠT6③:9)。有帶棱,弧形,尾部上端有一凸棱,下有一平面(ⅠT7③:9)。具有與現代意義的針相一致的使用功能。以遼河流域為腹地的遼東半島傳統文化和以黃河流域為腹地的大汶口文化,此時在遼東半島地區強強碰撞,使該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極為活躍。綜觀遼東半島出現的鬶、觚、盆形鼎和雙勾渦紋彩陶紋飾等,當是大汶口文化的早期主要特征⑦,這一時期也正是大汶口文化比較強盛的時期。
公元前3000年后以渤海南部為腹地的“區域”考古學文化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對小珠山遺址展開專題性發掘,其中比較重要的突破,就是在地層中甄別出含有“三堂一期”的文化層位⑧,進而從地層疊壓關系上確立了其在小珠山文化類型期別系統,即分期中的“第四期”。目前屬該期的遺址除三堂外,還有瓦房店交流島的蛤皮地、旅順大潘家早期(關于大潘家村遺址分期問題,原報告認為介于“小珠山中層、上層之間”。其實不然,若細檢地層與遺物,應有早晚之別,另文再論)、石灰窯、礪碴臺等⑨。這一期別的主要特征:陶器仍然以罐為主,還有缽和豆。陶質多為夾砂含云母黑褐陶和褐陶,體現在陶罐上,斂口,微鼓腹,口沿為三角形的泥條假疊唇。紋飾自口部始飾附加堆紋,在其上再飾平行線、短斜線、交叉紋、刺點紋、鋸齒紋等各種刻劃紋。腹部主要是縱向平行細泥條堆紋或橫向波浪形扁平附加堆紋。
該期土著文化因素明顯的同時,來自山東半島的文化因素依然存在,如小珠山遺址出土的缽(T1512④A:2、T1512④B:2)⑩、三堂一期的三足缽,前者具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后者又有白石村文化的因素。在大潘家遺址中還仍然有泥質紅陶上刻劃紋間繪紅彩。刻劃紋與紅彩組成復合紋,當可視為遷住與原住居民在社會層面上的融洽與和諧,及文化上的認同與融合的結晶。從這些含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來判斷,當屬大汶口文化晚期,也恰驗證了該期的相對年代,即公元前3000~前2800年(或稍晚些),進一步說明大汶口文化強勁北上始于其早期,而沒落于其晚期。大約沉寂一段時間后,便迎來了龍山文化時代。
小珠山第五期正是強盛的龍山文化時代時間段。曾有學者在全面考察郭家村上層出土的器物后,很有見地地提出了“山東龍山文化郭家村類型”。筆者經過多年思考和觀察,以為此觀點毋庸置疑。在認同的同時,我們將討論的是遼東半島地區此時何以成為“山東龍山文化郭家村類型”的考古學現象。首先是空間層面上。由于遼東半島處于遼河流域下游區域的邊際,東北腹地的邊陲———“天涯海角”,故文化的發展相對比較滯后,而傳統的東西成了桎梏創新的羈絆,久而久之,形成封閉的弱勢的單一文化狀態。在這種文化背景下,自然會招致新的文化影響和沖擊。其次是社會層面上。山東龍山文化通過一系列考古發現,文明因素紛紛涌現,且呈上升態勢,其社會進步勢不可擋。如在壽光邊線王、鄒平丁公及章丘著名的城子崖等地均發現龍山文化的城址瑏瑤。與此同時在郊縣三里河、棲霞楊家圈和日照堯王城等遺址還發現了龍山文化的銅器和冶銅渣等。這些跡象表明龍山文化正處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之中,而這種社會變革直接伴隨著社會的迅速分化與發展,導致該文化空前繁榮與發達,其強勢文化形成的張力表現出對外交往的活躍與擴張。
再次是文化層面上。文化上的發展趨勢必然是強勢文化的擴張和大遷徙。此時的遼東半島地區來自渤海南部的考古學文化因素紛紛涌進,在所發現的各文化遺址中大量出現了具有山東龍山文化特征的陶器,如四平山積石墓的、老鐵山積石墓MI(3)單耳杯、郭家村ⅡT4②:38鑿足鼎、上馬石ⅠT5④:41環足器、郭家村ⅡT7②:39圈足盤、ⅡT8②:39的甕、三堂二期ⅠT204④A:2缽、大潘家T3②:7提梁鈕器蓋等。具有土著特點的筒形罐處于頹勢,形態上變得更小,數量上變得更少,如郭家村ⅡT5F1:5、73T1F1:212等,而鼓腹罐呈上升態勢增多。通過上述分析,處于渤海南部的山東龍山文化其強勁的發展張力,必然導致它的發展空間向四周擴張遷移,而此時的遼東半島地區由于文化背景所致,自然也就成為它的發展勢力范圍,以至于成為以渤海南部為腹地的山東龍山文化北移文化區域“山東龍山文化郭家村類型”。
篇(5)
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論是考古學界還是錢幣學界,對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無專文論及。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筆者認為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
考古學斷代的方法在史前和歷史時期是不同的。歷史時期考古學斷代方法,除各時期考古通用之類型學、地層學外,還特別注重文字材料,如簡牘、銘文、碑志等等。在我國,錢幣用于考古斷代,僅適用于歷史時期。歷史上的錢幣均有各自的時代特征,這是利用錢幣進行斷代的理論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幣、刀幣、半兩、五銖、開元通寶等錢幣,一般無年號,但各種錢幣的行用均有時間范圍。綜上所述,出土錢幣為歷史時期考古斷代帶來了極大便利,成為考古學斷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時的注意事項
雖然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作用巨大,但在具體操作時有一些注意事項,否則可能得出錯誤結論。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層、遺跡、墓葬等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從理論上看,晚期單位(地層遺跡、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遺物,而早期單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遺物。因此,在晚期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見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錢幣的行用時間下限。一種錢幣的頒行時間是其行用時間的上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時代下限卻難以確定,因為頒行新幣后原來的錢幣并沒有立即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與新幣共同流通,有時流通時間還甚長,這在五銖、開元通寶等長壽錢身上體現特別明顯。
三、研究社會現實
錢幣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是財富的象征。在中國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觀念支下,不管高下貧富,人們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錢幣,這些錢幣有的是流通的實用幣,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幣。從隨葬錢幣的情況可以窺探當時社會現實,如社會盛衰、貧富分化、喪葬意識等等。錢幣是社會盛衰的一面鏡子,但利用出土錢幣進行社會盛衰研究,需要較多地依賴歷史文獻、社會背景來進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這方面多作論述。
一個墓葬是否厚葬,可通過陵墓大小、隨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體現。錢幣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隨葬品,也是體現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陽燒溝漢墓為例。該墓地的墓葬全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錢幣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錢幣約50枚¨。當然,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慮到歷史上被盜和自然破壞,其數目將更大。為讓讀者對50枚錢有個明晰的印象,我們可以簡單地看看當時人們的賦稅和生活狀況。西漢的人頭稅分算賦和口賦兩種,前者課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賦在西漢多時每人120錢,少時為40錢,口賦為23錢。東漢時繼承了西漢的算賦和口賦。因此,50錢相當于算賦的41.7%-125%,相當于口賦的2倍多。這個數據應該說是比較多的。
四、研究經濟文化交流
中國在歷史上多數時間都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從未中斷。錢幣作為支付、貯藏的手段,是貿易時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國境內出土了不少外國錢幣,如波斯薩珊朝銀幣、東羅馬和阿拉伯的金幣以及日本錢幣等等,在國外也出土過不少我國古錢幣,尤其是唐宋以來的錢幣。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異國錢幣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有力見證。出土的異國錢幣是研究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一種有效手段。學術界很早就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較豐碩。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紀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統計了當時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薩珊朝銀幣、阿拉伯金幣、東羅馬金幣等,并對其背景進行了探討。近年來,康柳碩先生《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拜占庭金幣綜述》《從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古代外國錢幣看絲綢之路上東西方錢幣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和羅豐先生的《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金幣》等文章也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幾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曉嵐《中外貨幣文化交流研究》是這方面研究的一本專著。
國外學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國F·蒂埃里c·莫里森的《簡述在中國發現的拜占庭金幣及其仿制品》等。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上述外國錢幣在新疆出土最多,這跟文獻記載相符合。《隋書》卷24“食貨志”記載:“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從新疆到關中的絲綢之路沿線均有外國錢幣發現,甚至在洛陽也有部分出土。據夏鼐先生統計,薩珊朝銀幣在中國已經出土2000枚以上,分屬十幾位王在位時期,時間跨度從4世紀至8世紀。在國外也有不少中國錢幣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國的五銖錢、貨泉以及后代的歷朝錢幣。有的地方出土數量很大,如寶冢市堂坂遺址出土了10萬多枚,而山口市大內遺址出土的則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鮮等地也曾出土過中國的古錢幣,散見于國內外的報道中,此不贅述。利用出土的異國錢幣固然是研究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筆者認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國影響而鑄造出的錢幣也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來的一個學術熱點,中國境內出土的外國錢幣、國外出土的中國錢幣以及能體現相互之間貨幣文化交流的錢幣材料都是有力的歷史見證,對它們的深入研究,必將推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古錢幣研究正方興未艾,越來越走向深入,與考古學的結合也日益緊密。
參考文獻:
篇(6)
錢幣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見之物 ,在考古學研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論是考古學界還是錢幣學界 ,對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無專文論及。筆者不揣淺陋 ,試對此作一粗淺的探討 ,望方家正之。
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筆者認為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斷代 ,二是研究當時社會現實 ,三是研究經濟文化交流 ,尤其是國際間的交流歷史。下面分別討論。
一、 斷代
(一)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
考古學斷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歷史時期是不 同的。歷史時期考古學斷代方法,除各 時期考古通用之類型學、地層學外,還特別注重文字材料,如簡牘、銘文、碑志等等。在我國,錢幣用于考古斷代,僅適用于歷史時期。
歷史上的錢幣均有各自的時代特征,這是利用錢幣進行 斷代 的理論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幣、刀幣、半兩、五銖、開元通寶等錢幣,一般無年號 ,但各種錢幣的行用均有時間范圍。如布幣、刀幣行用于春秋戰國時期,蟻鼻錢行用于戰國時期 ,半兩錢行用于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時期。上述錢幣又可分為不同的類別,均各有其行用時間。如“八銖半兩”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鑄,“四銖半兩”為漢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鑄。其他如貨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錢幣、蜀漢直百五銖、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錢幣,均有較明確的行用時間,不必一一列舉。
五銖錢,始鑄于西漢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廢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國古代行用時間最長的貨幣 ,歷時七百多年,被譽為“長壽錢”。經學界各代達人 的努力 ,五銖錢的斷代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蔣若是先生《洛陽燒溝漢墓》一書。蔣氏利用大量的漢墓材料,結合文獻記載將漢代五銖錢分成五型。雖然其中某些細節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結論經半世紀的考驗 ,仍無大謬,受到學界的高度贊揚。在撰成《洛 陽燒溝漢墓》幾十年后蔣先生又完成《秦漢錢幣研究一書,該書集蔣先生幾十年研究秦漢錢幣的心得,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此外,北京大學吳榮 曾先生撰有《五銖錢 與墓葬斷代》一 文,對磨郭錢、五銖小錢的斷代進行了深入研究 ,頗 有說服力 。今 日,兩漢五銖的斷代已經不存在較大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政權更迭頻繁、地方政權并立 ,因此 ,貨幣的發行混亂不堪 ,多數貨幣行用不久即頒行新幣人們可能認為,這個時期幣制如此混亂,斷代研究可能會很難 ,其實恰好相反。原因很簡單,每種錢幣行用的時間不長,正好更準確的表明了該錢 幣的所屬時間。如梁 四柱五銖 ,錢面上下各 有二星,頗具特征。又如南朝宋 文帝鑄重 達八 銖之 五銖錢 ,世稱“當兩五銖”。這些錢幣的時代特征明顯 ,于斷代十分有利。隋五銖外郭特寬、錢色泛白、“五”字旁有一豎 ,特征鮮明,易于判別,且行用時間較短,故斷代價值較高。
“開元通寶”錢也是一種長壽錢 ,始鑄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為主幣沿用至五代十國時期甚至清代農 民政權也 曾鑄行此錢。唐、五代所行“開元通寶”品種達數 十種,其 區別主要體現在字形變化上。目前學術界已能大致區別 出不同時代之“開元通寶” 。
宋代以來,年號錢盛行 ,往往每次改年號 ,都要發行新的年號錢,此已為學界常識,不必多言。年號錢的發行為考古斷代提供 了極大的方便,使斷代能更為精確。僅舉一例 :廣西賀州博物館 2002年在對臨賀故城進行維修時 ,發現一座出土“元豐通寶 ”的墓葬打破紅色磚墻 的情況 ,從而判斷出紅色墻磚 的時代在北宋元豐年間以前。后來再結合文獻記載的時期曾對城墻進行過較大工程的情況推測該段城墻為南漢所修 。這樣 的例子在 考古工作 中屢見不鮮,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 ,出土錢幣為歷史時期考古斷代帶來了極大便利,成為考古學斷代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錢 幣進行考古斷代時的注意事項
雖然利用 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作用巨大,但在具體操作時有一些注意事項,否則可能得出錯誤結論。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層、遺跡、墓葬等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從理論上看,晚期單位(地層遺跡、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遺物 ,而早期單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遺物 。因此,在 晚期單位 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見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錢幣的行用時間下限。一種錢幣的頒行時間是其行用時間的上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時代下限卻難 以確定,因為頒行新幣后原來的錢幣并沒有立即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與新幣共同流通 ,有時流通時間還甚長,這在五銖 、開元通寶等長壽錢身上體現特別明顯。筆者在研究三峽地區秦漢墓時發現:秦半兩、漢初榆莢半 兩、文帝 四銖半兩等半兩錢均沿用至西漢 中期,武帝五銖沿用至東漢中期 ,昭宣五銖沿用至東漢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貨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東漢 晚期的情況 。管維 良先生曾對魏 晉南北朝 時期 四十批墓葬和窖藏 中的出土的錢幣進行分析統計。結果如下:三國吳的六批材料中漢五銖錢在所有 出土錢幣中所占比例最低為 33%,最高為 100%,絕大多數時候為 90%以上。兩晉 的十六批材料 中有 十四批 出土漢五銖 ,所占比例最少為 33% ,最高為 100%,有7批。絕 大多 數為 90%以上 。南朝 5例 ,分別為100%、8%、100%、95%以上、66%。北齊 6例 ,僅一例出土錢幣3枚,其中漢五銖 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統計中,出土錢幣較多墓葬 中漢五銖的數量均在 90%以上 ,可見 ,當時流通 的主要貨 幣應該 是漢五銖,只是到北齊前后 ,漢代五銖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筆者認為,各種錢幣的實 際行用時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
在上面兩種情況下,如果僅僅依靠錢幣進行 斷代就有可能會拔高時代 ,造成斷代失誤。為此 ,須堅持兩個原則 :其一,在出土不 同時代錢幣的情況下,應以時代最晚材料作為斷代標準;其二,錢幣材料要與其他材料 ,如地層關系、墓葬形 制、器物、碑志 、銘文等等結合分析。須知 ,錢幣材 料僅是 斷代的一個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們既要重視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過分夸大。
二、研究社會現實
錢幣作為一種特殊 的商品,是財富的象征。在中國古代“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觀念支下 ,不管高下貧富 ,人們都要往墓 中放置一些錢幣,這些錢幣有的是流通 的實用幣,也有的是非流通的 冥幣。從隨葬錢幣的情況可 以窺探 當時社會現實,如社會盛衰、貧富分化、喪葬意識等等。錢幣是社會盛衰的一面鏡子 ,但利用出土錢幣進行社會盛衰研究,需要較多地依賴歷史文獻 、社會背景來進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這方面多作論述。
墓葬中隨葬錢幣的多少可以反映社會上貧富分化的程度。以筆者 曾研究 過的三峽地 區秦漢墓為例,西漢早期的 11座墓葬 中,其 中 2座沒有出土任何錢幣,其余 9座分別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 、113枚、173枚 ,共 5l4枚,這 11 座墓平均每座約 47枚。西漢武 昭時期 墓 葬共 27座 ,其中沒有出土任何錢幣的有 9座,出土情況不詳的有 3座,除此 以外的 15座墓葬 ,出土錢幣最少的是 2枚 ,最多的是 1042枚 ,總數約 2200枚 ,除去不詳的3座,其余 44座平均約50枚 。
從上述數據看 ,各墓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最少的連 1枚錢幣也沒有 ,最多 的達到上千枚。據研究 ,出土 1000余枚錢幣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級官員或其家人的墓葬。雖然 由于保存狀況的不 同,有的墓葬出土錢幣數與實際隨葬數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納人統計的墓葬數量較多,上述結論應當還是可信的。
為顯示孝道 ,加上相信人死后還會在另一個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間的一切,因此,古人們往往不惜花費巨資,為死去的親人打造一個類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謂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漢代是一個 崇 尚厚 葬 的時代 。西漢時期的《鹽鐵論》“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于寢 ,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后,則封之,庶人 之墳半 仞,其 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恩。”[9](p2s3)時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 ,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橘梓梗楠,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 ,廣種松柏,廬舍祠堂 ,崇侈上僭”¨。
一個墓葬是否厚葬,可通過陵墓大小、隨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體現。錢幣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隨葬品,也是體現是否厚葬 的一 面窗 口。以洛 陽燒溝漢墓為例。該墓地的墓葬全為中小型墓 ,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錢幣 11265枚 ,平均每墓出土錢幣約 50枚¨ 。當然,這只是考古 出土 的,如考慮到歷史上被盜和 自然破壞 ,其數 目將更大。為讓讀者對 50枚錢有個明晰的印象,我們可以簡單地看看 當時人們的賦稅和生活狀況。
西漢的人頭稅分算賦和 口賦兩種,前者課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賦 在西漢多時每人 120錢 ,少時為 40錢 ,口賦為 23錢。東漢時繼承了西漢的算賦 和 口賦。因此 ,50錢相當于算賦的 41.7%-125%,相 當于口賦的 2倍多。這個數據應該說是比較多的。
我們再看看當時人們在算賦和 口賦下的生活狀況。《漢書 ·貢禹傳》云 :“武帝征伐四夷 ,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輒殺。”賦稅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貧化 ,進而導致社會極大動蕩。每座墓葬同樣平均出土 50枚錢幣的三峽地區情況又是如何呢?東漢晚期三峽地區流行一首謠諺 :“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鄰家貸,鄰人已言匱。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在活人生活 尚且如此困頓的情況下 ,人們還情愿拿出這么多的錢幣來為死人隨葬 ,可見厚葬風氣之盛。
三、研究經濟文化交流
中國在歷史上多數時間都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從未中斷。錢幣作為支付、貯藏的手段,是貿易時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國境內出土了不少外國錢幣,如波斯薩珊朝銀幣、東羅馬和阿拉伯的金幣以及 日本錢幣等等,在 國外也 出土過不少我國古錢幣,尤其是唐宋以來的錢幣。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異國錢幣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有力見證。
出土的異國錢幣是研究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一種有效手段。學術界很早就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較豐碩。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紀 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統計 了當時 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薩珊朝銀幣、阿拉伯金幣、東羅馬金幣等,并對其背景進行了探討 。近年來,康柳碩先生《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拜占庭金幣綜述》《從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古代外國錢幣看絲綢之路上東西方錢幣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和羅豐先生的《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金幣》等文章也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 前幾年出版 的戴建兵、王曉嵐《中外貨幣文化交流研究》是這方面研究的一本專著。
國外學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 國 F·蒂埃里 c·莫里森的《簡述在中國發現的拜占庭金幣及其仿制品》等。
根據 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上述外國錢幣在新疆 出土最多,這跟文獻記載相符合。《隋書》卷24“食貨志”記載:“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從新疆到關中的絲綢之路沿線均有外國錢幣發現,甚至在洛陽也有部分出土。據夏鼐先生統計,薩珊朝銀幣在中國已經出土 2000枚 以上,分屬十幾位王在位時期,時間跨度從 4世紀至 8世紀。在國外也有不少中國錢幣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國的五銖錢、貨泉以及后代的歷朝錢幣。有的地方出土數量很大,如寶冢市堂坂遺址出土了10萬多枚,而山口市大內遺址出土的則有250公斤 。
另外在越南、朝鮮等地也曾出土過中國的古錢幣,散見于國內外的報道中,此不贅述。利用出土的異國錢幣固然是研究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筆者認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國影響而鑄造出的錢幣也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例如,古代 中國的周邊 國家 ,如朝鮮、日本、越南、泰國等國在歷史上都曾仿照中國鑄造圓形方孔錢。如 日本曾仿鑄南唐的“唐國通寶”“至道元寶”越南曾仿鑄 “開元通寶”“元占通寶”“天禧通 寶”“至道元寶”“元符通寶”等等。此外,在絲綢之路沿線如新疆、中亞等地出土的一些錢幣帶有明顯的東西方貨幣文化交融的特點。如:古于闐國鑄造的漢二體錢(俗稱“和田馬錢”)、古龜茲國鑄造的漢龜二體錢 、回鶻錢、察合臺錢幣等都屬此類。
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來的一個學術熱點 ,中國境 內出土的外國錢幣、國外 出土的中國錢幣以及能體現相互之間貨幣文化交流的錢幣材料都是有力的歷史見證 ,對它們的深入研究 ,必將推進 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古錢幣研究正方興未艾,越來越走向深入 ,與考古學的結合也 日益緊密。本文粗略討論了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三個方面的作用 ,權作引玉之磚 。
參考文獻 :
[1] 洛陽區考古隊.洛 陽燒溝漢墓[M].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59.
[2] 蔣若是.秦漢錢 幣研究 [M].北京 :中華書局,1997.
[3] 吳榮曾.五銖錢與墓葬斷代[EB/OL].http://www.zisi.net/htm/ztlw2/zggds/2005—05—10—20687.htm.
[4] 齊東方 .隋唐考古 [M].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4.
[5] 胡慶生.賀州市博物館利用錢幣進行考古斷代的兩例報告[J].廣西金融研究,2003,增刊2.
[6] 蔣曉春.三峽地區秦漢墓研究 [D].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7] 管維 良.“五銖 錢與“五銖時代 ”淺論 [A].重慶市錢幣學 會.重慶錢幣研究文集[C].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
[8] 蔣曉春.三峽地區秦漢墓研究 [D].四川 大學博士學位論 文,2005.
[9] 王貞珉注譯,王利器審訂.鹽鐵論譯注[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10] 王符(清 ·汪繼培箋).潛夫論 ·浮侈第十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燒溝漢墓[R].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12] 常 璩 (劉琳校注 ).華 陽國志 ·巴志[M].成都:巴蜀 書社,1984.
[13] 夏 鼐.咸陽底張灣隋墓出土 的東羅馬金幣 [J].考古學 報,1959,(3).西安土門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幣[J].考古,1961,(8).西安出土的阿拉伯金幣[J]考古 ,1965,(8).綜述 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J].考古學報。1974,(1).近年中國出土的薩珊朝文物[J],考古 ,1978,(2).
[14] 康柳碩.中國境內出土發現 的拜 占庭金幣綜述 [J].中國錢幣,2001,(4).
[15] 康柳碩.從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古代外國錢幣看絲綢之路上東西方錢幣文化的交流與融合[J].甘肅金融,2002,(2).
[16] 羅 豐.中國境內發 現的東羅馬金幣 [A].中外關系史 ·新史料與新問題[c].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篇(7)
[中圖分類號]K8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57(x)(2012)03—0049—08
一、青藏高原早期人類及其石器的古老性
從上世紀初以來,藏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及考古學的學者們,不間斷地努力探索著青藏高原的史前文明,然而由于空間上的距離和海拔上的高度,更加之時間上的悠遠,我們在認知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道路上,依然腳步蹣跚。
地理學認為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輕的高原,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后隆起并形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地方。青藏高原的隆起過程大約從1000多萬年前開始,至今尚未完全結束。元代藏族文獻《紅史》用藏族自己的語言,對這塊最年輕的高原給予形象而準確地描述:“三千世界形成之時,世界為一大海,海面上有被風吹起的沉渣凝結,狀如新鮮酥油,由此形成大陸。”
考古學家不這么認為。在考古學家眼里,青藏高原一度是一塊與人類起源相關的古老土地。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神秘性,給學者們帶來了巨大的遐想空間。上個世紀初,當時其史前文化尚不為人知的青藏高原被認為有可能是人類最初的發源地之一。20世紀前半葉,英國、德國和前蘇聯學者認為,第三紀晚期喜馬拉雅山急劇上升,蒙藏地區森林消退,從而迫使人類遠祖——古猿從森林轉入地面生活,逐漸變成現代人。在上個世紀中葉,特別是青藏高原東南邊緣的云南元謀發現距今170萬年的猿人化石以后,青藏高原人類起源的觀點在中國學術界再次被重申。已故的著名人類學家賈蘭坡認為:“正當從猿變到人期間,青藏地區仍然是適合人類演化的舞臺,到那里尋找從猿到人的缺環也是有希望的。”著名的考古學家童恩正也認為:“中國的西部,特別是高原及其鄰近地區,有可能是從猿到人進化的搖籃。”直到上個世紀末,乃至本世紀初,我國仍有許多學者在堅持和恪守這個說法。 考古學家的說法并非想要聳人聽聞,上個世紀下半葉以來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似乎為人類青藏高原起源說提供著物質證據。考古學家們決心要找到青藏高原的“第一把石刀”,因為對于旨在建立時空框架的傳統考古學來講,找到這個序列的起始點是至為關鍵的第一步。
篇(8)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對于歷史文化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時代,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學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學科互涉”的性質,形成了美術考古學。與其他學科相比,此學科兼具美術學和考古學兩方面的特點,對美術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研究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方法論和結構,探討二者之間的滲透和交叉關系,對各學科的研究邊界進行討論具有重要意義。
一、古物學對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影響
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多個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較為明顯的是,二者在發展過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學的重要影響。無論是在中國古代還是在西方國家的發展歷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習慣,中國古代存在著“玉府”等收藏古物的專有機構;外國的皇族對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當時古物學發展的動力。
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真正開始交叉滲透的時間是在18世紀中期,溫克爾曼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其著作《古代美術史》的研究內容主要是針對美術的發展歷史。該學者在編寫的過程中,從美術史的角度出發,對促進民族發展的古物和記載美術史的古物文獻展開了研究。正是因為該學者將古物學和美術史學、考古學結合起來,才發現總結出美術的發展歷程,促使了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成熟,溫克爾曼也因此被稱為“美術史學之父”和“考古學之父”。無論是溫克爾曼的稱謂還是其著作的特點,都向我們反映了一個信息:美術史學與考古學之間都受到古物學的影響,二者之間具有很大的聯系。
二、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相互滲透和了解
不同學科之間跨越了邊界之后就會產生互相滲透,即產生我們所認為的“學科互涉”。許多學者認為這種滲透是必然的,不同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叉主要體現在學科的認知方向和知識體系等方面;學科的指導思想、理論和研究方法;與學科相關的社會和技術問題;與其他學科產生的滲透和交叉性;學科內外的定義等。美術史和考古學學科互涉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學科的認知方向和知識體系
無論是考古學還是美術史學,在對相關的方法和對象進行論述和解釋時,都涉及大量的說明和闡釋,此特點表明了人文學科的鮮明特點。若根據研究對象來進行劃分,美術史學屬于美術學的范疇;若根據研究體系來看,美術史學又屬于歷史學。在美術史學的發展中,人類的審美情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較為濃烈,理性認識的實現也需要通過感官來進行。我們可以將美術史學的研究實質歸結為:通過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風格來認識美術家或者是史學家的思想感情,從而探索其中蘊含的發展規律[1]。
與美術史學的不同之處在于,考古學直接強調理性在研究和發展中的作用,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人類的發展,通過分類描述遺留的物品來對古代社會的存在形式進行研究,并研究遺留物品之間的關系,從而確定相關的功能,此外,對遺留物品的發展和改變進行研究和分析,能夠了解古代社會發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關發展的具體意義。無論是探索背后的規律還是直接將理性思想運用于分析和調查中,考古學和美術史學的發展和研究都是將探索和研究物質世界作為主要的研究途徑和方向來實現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產生的交叉
考古學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為研究地層和器物的類型。20世紀中期的考古學主要局限于單純的研究和記錄,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內容就是對地層以及器物的類型進行研究和總結。直到1960年之后,丹麥的著名學者克里斯丁在對古典的器物進行研究時,融入了情境,并對器物的裝飾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這不僅對考古學的發展有促進作用,對美術史學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參考作用。之后蘇秉琦也利用了美術的圖案分類將美術的寫實與寫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學中。
在美術史學中也有考古學的滲透,例如,廣泛應用于年代和類型的研究方法同樣能夠為美術史學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對美術的風格進行研究時,法國的夏皮羅采用了層析法進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層析分別是對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間的關聯進行的研究,與考古學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圍內,這種學科互涉的現象都非常普遍,外國學者溫克爾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學科互涉。在我國的古代,學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為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貢獻[2]。
(三)研究對象的滲透和交叉
從研究對象來看,美術史學和考古學之間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滲透。美術史學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美術的作品以及美術作品的創作者,尤其是在對古代的美術作品進行研究時,涉及的研究對象往往都屬于考古學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由此可見,考古學和美術史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資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畫、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藝品等等。對人類古代遺跡進行研究和保存是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共同面臨的重要問題。
(四)學科結構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術史學與考古學在自身的學科結構等方面也有相似之處。
若根據美術史學的學科性質來進行分類,可以分成歷史和藝術等方面的課程,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大類:美術基礎實踐,主要是指對美術的基本技能進行的練習和創作等,目的是加強素描、繪畫等基本的美術技能;美術史論,是指對美術的歷史和評論等方面的學習,目前出現的課程分類主要包含文物的保護以及鑒定、藝術作品評論、藝術作品鑒賞、文藝理論等方面,其中的文藝理論課程和文物相關的課程都與考古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相關數據表明,美國早在20世紀中期就開設了多種美術和藝術史課程,涉及的范圍也較廣,初步統計已經達到了800種。這些新設立的課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課程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并設立的,為學生學習文物的維護和修復提供了一定的美學基礎[3]。
從考古學的結構出發,除了對基本的文物展開研究之外,對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術知識。此外,考古學涉及社會、文學、美學等多個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種其他學科,例如地質學、建筑史學、體質人類學、醫學等,對多個學科的發展都有著相互促進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學就包含在美術史學中。因此,二者在結構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4]。
三、美術考古學的形成
在當今信息化時代的發展背景下,學科互涉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就目前而言,考古學家在進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時,已經涉及了大量的美術史學的資料和方法。同樣的,美術史學家在對美術歷史進行研究的同時,也使用了考古學中的大量資料,各專家的研究視角越來越廣,概念也越來越寬泛。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和實踐,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交叉滲透已經促使一個新的學科形成,即美術考古學。該學科是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廣泛全面的研究內容、對象以及方法論。
四、結語
隨著社會的逐步發展,各個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流會越來越頻繁,信息化的發展為學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當今的學者必須利用好各種有利的條件,加深對各個學科邊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進各學科的共同進步和發展。
【參考文獻】
[1]賈玉平.從“學科互涉”看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2(06):88-95.
篇(9)
商湯滅夏后,商王朝五遷其都,最終定都今河南安陽小屯(即“殷墟”),直至被周族所滅,歷經六百年左右。商王朝的歷史是我國燦爛的青銅文化逐步發展到高峰的歷史,也是我國奴隸制社會逐步上升的歷史。根據商代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以商王盤庚遷都至殷為界,將商代文化分為前后兩個時期,盤庚以前的早商文化為商代前期,盤庚和盤庚以后的晚商文化為商代后期。商代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如東下馮商城遺址、垣曲商城遺址、平陸前莊出土的青銅器等,是與典型的商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遺存。它們主要分布在靠近商王朝都城的黃河北岸及臨近地區,這些地區可能屬商朝的直接統治范圍之內。他們的經濟生活與商相同,以農耕經濟為主,同時經營家畜飼養和漁獵。垣曲商城,位于古城南關村西側的黃土臺地上,垣曲商城是以層層夯土修筑的由四面城垣圍成的方形城堡,平面形狀略呈梯形,北窄南寬,總面積13萬平方米。城址內中部偏東為統治者居住的宮殿區,由多座大型夯土臺基組成,以南北并列的兩座長方形大型臺基為中心,其余分布在其周圍,形成一組基址群,臺基四周有長方形宮城墻將宮殿區圍在中間。城內東南部為一般居民區,是平民進行生產與生活的主要活動區,分布著大量儲存物品的窖穴和堆積廢棄物的灰坑等。
城址內西南部為制陶手工業作坊區,發現有多座制陶窯址。垣曲商城出土遺物主要為陶器,陶質以夾砂陶為主,紋飾常見繩紋且形式多樣,有粗繩紋、細繩紋、間斷繩紋、交錯繩紋等,主要器形有折沿實尖足鬲、大口尊、平沿盆、罐、豆,其他遺物有銅鼎、銅斝、銅爵等,屬于商代二里岡期文化,與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年代相當。垣曲商城毗鄰商王朝中心區域,其建筑規模遠小于王都,因此有可能只是區域性的統治中心,或是商代分封于此的某方國的都城。也可能是據守黃河岸邊的一座軍事城堡。東下馮遺址發現的商城,位于運城盆地西緣,城址平面大體方形,面積14萬余平方米。出土陶器有鬲、簋、罐、甗、大口尊、蛋形甕等,還出土了銅爵、銅刀、銅鏃。與垣曲商城規模相當,可能是一方國之都或商朝設在晉南的一座軍事據點。平陸縣前莊村出土的一批商代文化遺存,其青銅器多立耳、深腹、空心柱狀足,飾簡單的饕餮紋,具有商代前期銅器的典型特征。陶器有鬲、大口尊、三足甕、簋等,也有鉆、灼、鑿的無字甲骨。垣曲、東下馮和前莊三處遺址,屬于黃河北岸的軍事重鎮,對于保障商西部疆域具有戰略意義。平陸前莊等地出土的青銅重器,更可說明這些地方與商王朝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晉西南、乃至晉南、晉東南與商朝王都毗鄰的部分地區都是商朝的勢力范圍,是商王朝的經略要地。山西商代后期的商文化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分布在臨汾盆地以東至晉東南地區的長子、潞城和黎城等地,與河南殷墟相鄰,文化面貌一致,以浮山橋北商墓、長治小神遺址、長子北高廟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為代表;另一部分是方國文化。浮山橋北商代墓葬,位于臨汾盆地東南緣。被盜嚴重,追繳回文物中有帶“先”銘的商代銅器。2003年發掘清理大型墓葬5座,其中M1、M18規模較大,墓道中有隨葬的殉人及車、馬。墓主人應當是商王朝管轄下的方國首領。盤庚遷殷以后,長治小神村商代遺址出土商代陶器鬲、豆、罐、甕等,與殷墟文化接近,分布范圍包括長治、晉城兩個小盆地。北高廟遺址發現銅器19件,主要有鼎、斝、爵、甗、觚、罍、鬲、戈、鏃等。特點是,仿陶器占一定數量,斝平底,鼎、甗錐足;紋飾簡單,以單層饕餮紋、珠紋、弦紋等為主,與小神商代遺存屬同一文化類型。
山西中西部呂梁山和沿黃河一線,當時存在著與商王朝若即若離的眾多“方國”,甲骨文多見記述。靈石、石樓、柳林和保德等地從五十年代開始,陸續發現過大量商代晚期青銅器。這種文化遺存,既受商文化的強烈影響,同時又受北方草原青銅文化即北方系青銅文化的影響,再加上本身具有的特征,形成一種混合的文化遺存。他們可能代表著存在于當時山西境內若干方國的文化,它占據著山西的大部分地區,應是山西境內商文化的主流。這些方國雖然也有定居聚落,也有農業經濟,但主要是一種游牧式的經濟,這和他們生活的地理環境有關,從考古發現的許多工具中也能看到這一點。靈石旌介村商墓出土的晚商青銅器以中原青銅器為主,有鼎、觚、爵、卣、簋、直內戈、有鋌鏃等,組合以爵、觚酒器為主,同時有鼎、簋的搭配。形制、花紋與組合均體現出殷商文化的特點,但弓形器、羊首刀、有銎鉞等又有北方系青銅器文化的某些特征。因此,旌介商墓青銅器為代表的文化系統應是商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吸收、融合當地及其他青銅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一個地域類型或是商文化的一個分支,是與商王朝有著較為穩定的臣屬關系的方國的遺存。這一類型遺存在晉中太谷白燕、忻州連寺溝等地均有發現。旌介商墓墓坑形制均為長方形豎坑土穴,流行在二層臺上殉人和在窯坑中殉犬的習俗同于殷墟墓葬的喪葬禮制,而且其青銅風格和殷商文化的也一致,暗示鬲方與商朝的友好。除鬲方之外,山西還有許多與商朝友好的方國,見于甲骨文和金文的有天、戈、邑、子等10余個,其地域大多在晉南和晉東南。
篇(10)
關鍵詞:百色地區;新石器時代;動物考古
一、前言
動物考古學(z00archaeology),亦稱“骨骼考古學”或“考古動物學”,是指對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遺存進行分析和研究的學科。研究目標包括復原古代環境,研究人類行為,研究人類與環境、人類與其它動物群體之間的關系等,最終目標是從動物遺存的角度復原古代社會。
本文研究的對象主要為來自廣西百色地區三個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動物遺存。這三個遺址分別為:革新橋、百達和坎屯,均為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來發掘所獲。考古隊員在發掘的過程中使用了浮選的方法,全面系統的進行了動物遺存的采集工作,為后期室內整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之所以選擇這三個遺址進行比較研究,主要原因如下:從地理位置上來說,這三個遺址均相距不遠,尤其是百達和坎屯遺址同屬陽圩鎮:從時代上來說,三個遺址均屬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石制品面貌顯示出來的特征表明三者在絕對年代上稍有先后:從聚落特征來看,三個聚落的性質及復雜程度各有不同,顯示出明顯的差異:從研究方法上來說,三個遺址的動物遺存全部由筆者進行整理,在整理的過程中使用了相同的鑒定標準和統計手段,方便進行比較研究。我們是將動物遺存看作聚落考古研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力圖從動物遺存的角度進行聚落特征相關的比較研究。
二、動物遺存概況
1、革新橋遺址②
發現動物遺存共12349件,其中可鑒定標本2637件。哺乳動物最小個體數為58。已經鑒定出來的種屬包括有:水鹿、斑鹿、麂、麝、牛、豬、犀牛、獼猴、象、豪豬、竹鼠、豬獾、黑熊、龜、鱉、鯉魚、青魚、草魚和鮑魚等。
動物遺存在出土時集中分布于特定的區域內(圖一),這一現象可能是當時先民集中消費動物資源的一種反映。
研究結果表明,革新橋先民們已經開始飼養家豬了,部分測量數據表明,此時的家豬在形態上可能還有些像野豬,處于馴化的初始階段。
從動物構成情況來看,全部可鑒定動物種屬中數量最多的是哺乳動物,魚、鳥和爬行動物都比較少(圖二),軟體動物僅發現少量殘骸(難以確定種屬和數量,故原鑒定報告在統計數量時并未將其包含在內)。
主要的哺乳動物,從可鑒定標本數來看,以野生的鹿類動物為主(72%),家豬僅占14%(圖三);從最小個體數來看,也是以野生的鹿類為主(58%),家豬僅占16%(圖四);而從肉食量來看③,是以野生的牛為主的(55%),野生的鹿類占了19%,家豬也僅占19%(圖五)。
2、百達遺址
發現動物遺存共25516件,其中可鑒定標本17811件。哺乳動物的最小個體數為60。已經鑒定出來的動物種屬包括有:大型鹿、中型鹿、麂、小型鹿、牛、豬、狗、豬獾、獼猴、犀牛、熊、倉鼠、竹鼠、麗松鼠、河貍、豪豬、兔子、鳥、鯉魚、青魚、鰱魚、鮑魚、龜、鱉、鱷魚、背瘤麗蚌、蚌、螺、蟹等。
研究結果表明,百達遺址除了豬④和狗可能是已經馴化的家畜外,其它動物均為野生,野生動物種屬極為豐富。
從動物構成來看,全部動物中哺乳動物(37%)和魚類(40%)比例相當,占了主要地位,鳥、軟體動物和爬行動物都比較少,此外還有少量節肢動物發現(圖六)。
主要的哺乳動物,從可鑒定標本數來看,以野生的鹿類動物為主,優勢非常明顯(88%),家豬僅占4%(圖七);從最小個體數來看,也是以野生的鹿類為主(58%),家豬僅占5%(圖八);而從肉食量(標準參考上文)來看,是以野生的鹿類(44%)和牛(33%)為主的,家豬僅占12%(圖九)。
3、坎屯遺址
發現動物遺存共2333件,其中可鑒定標本1212件,哺乳動物最小個體數為32。已經鑒定出來的動物種屬包括有:大型鹿、中型鹿、麝、麂、犀牛、牛、豬、豬獾、狗、貓科、兔子、豪豬、獼猴、龜、鱉、鱷魚、圓頂珠蚌、田螺、環棱螺、塔錐短溝蜷、蚌、鯉魚、鮑魚、魚、蟹、鳥等。
研究結果表明,坎屯遺址除了豬⑤和狗可能是已經馴化的家畜外,其它均為野生動物。
從動物構成情況來看,全部動物中哺乳動物數量上占了明顯優勢(68%),魚、軟體動物和爬行動物都比較少,此外還有少量鳥和節肢動物發現(圖一O)。
主要的哺乳動物的,從可鑒定標本數來看,以野生的鹿類動物為主(82%),家豬僅占5%(圖一一);從最小個體數來看,也是以野生的鹿類為主(74%),家豬僅占3%(圖一二);而從肉食量(標準參考上文)來看,是以野生的牛(47%)和鹿類(38%)為主的,家豬僅占4%(圖一三)。
三、討論與分析
(一)動物群